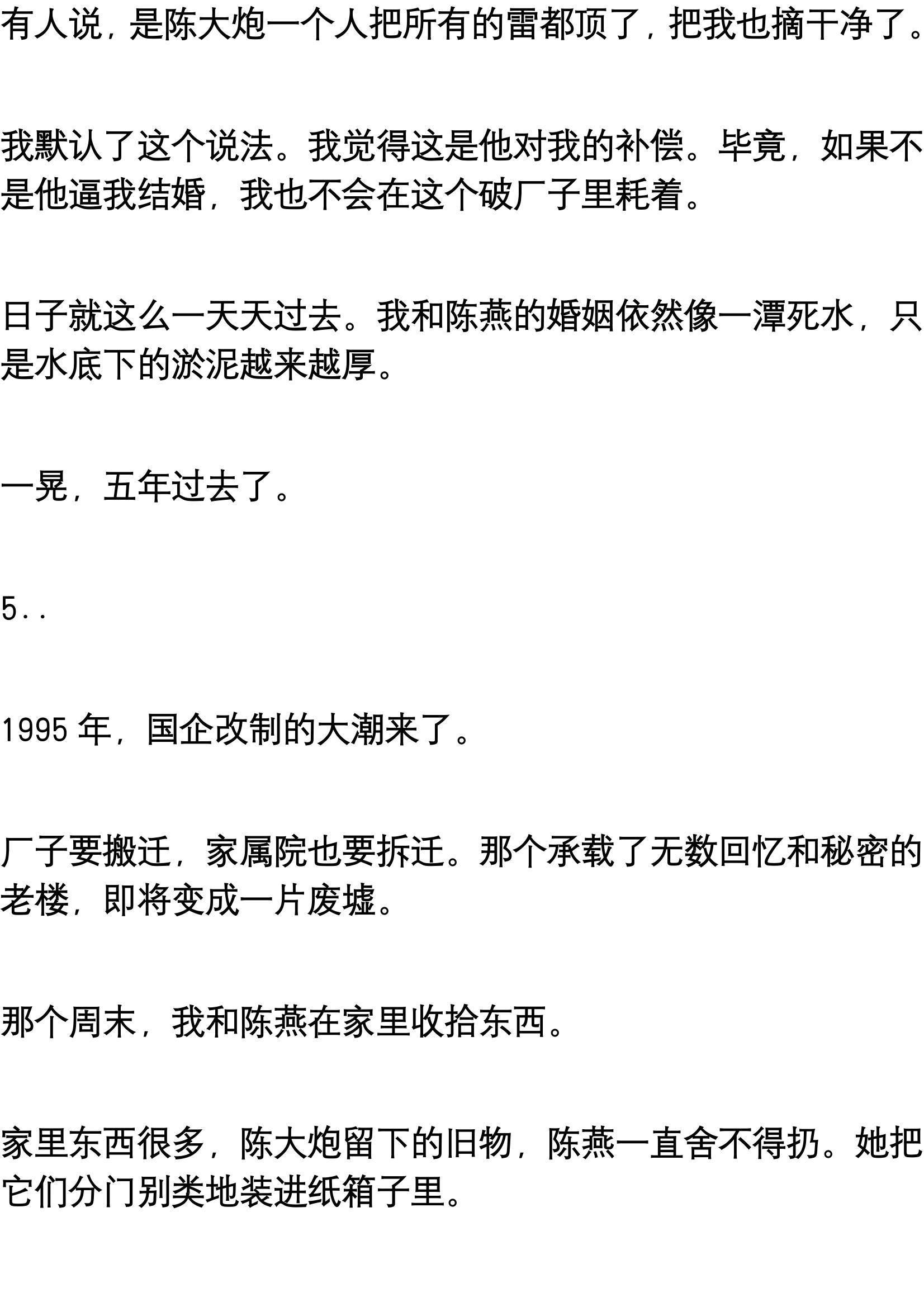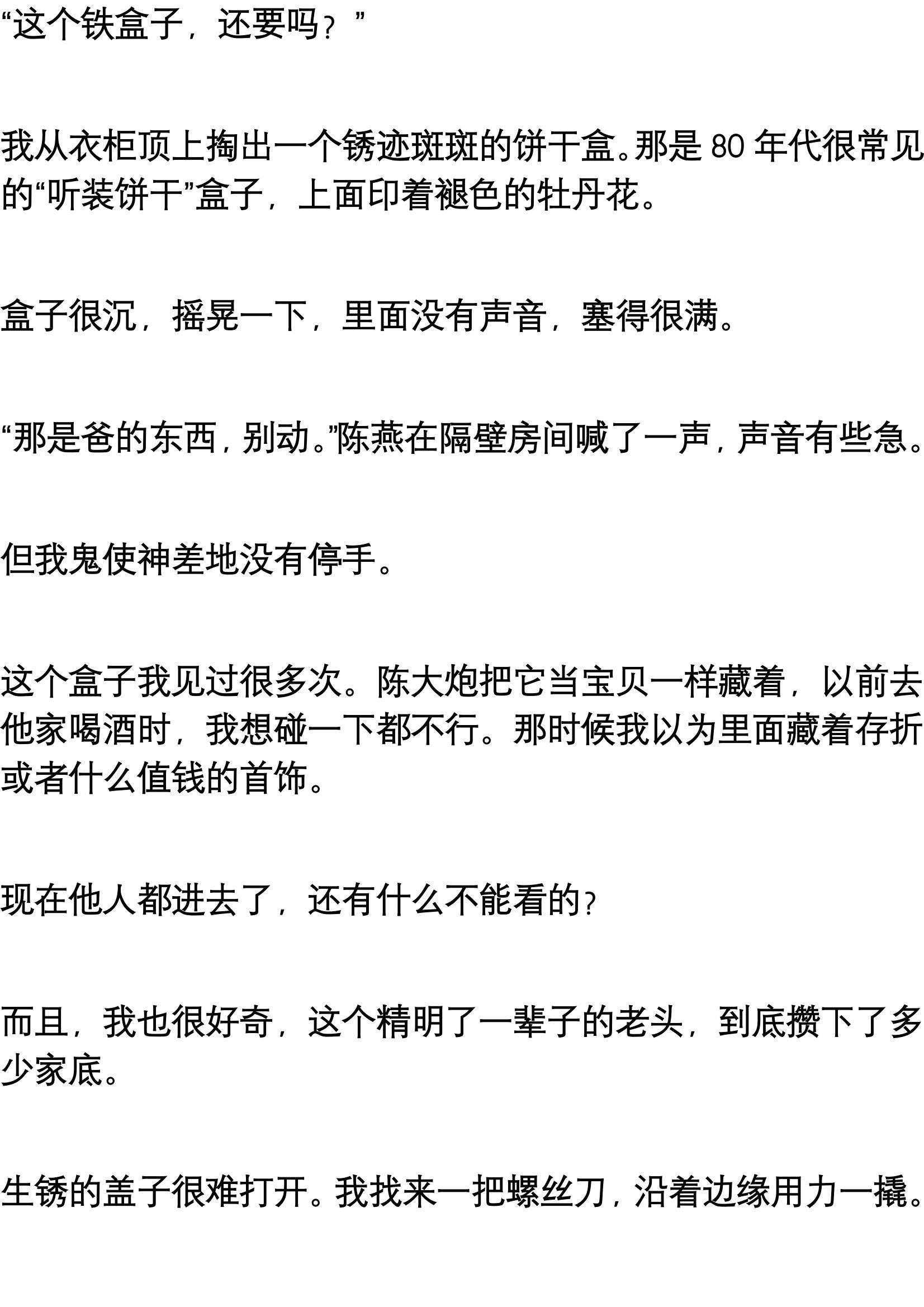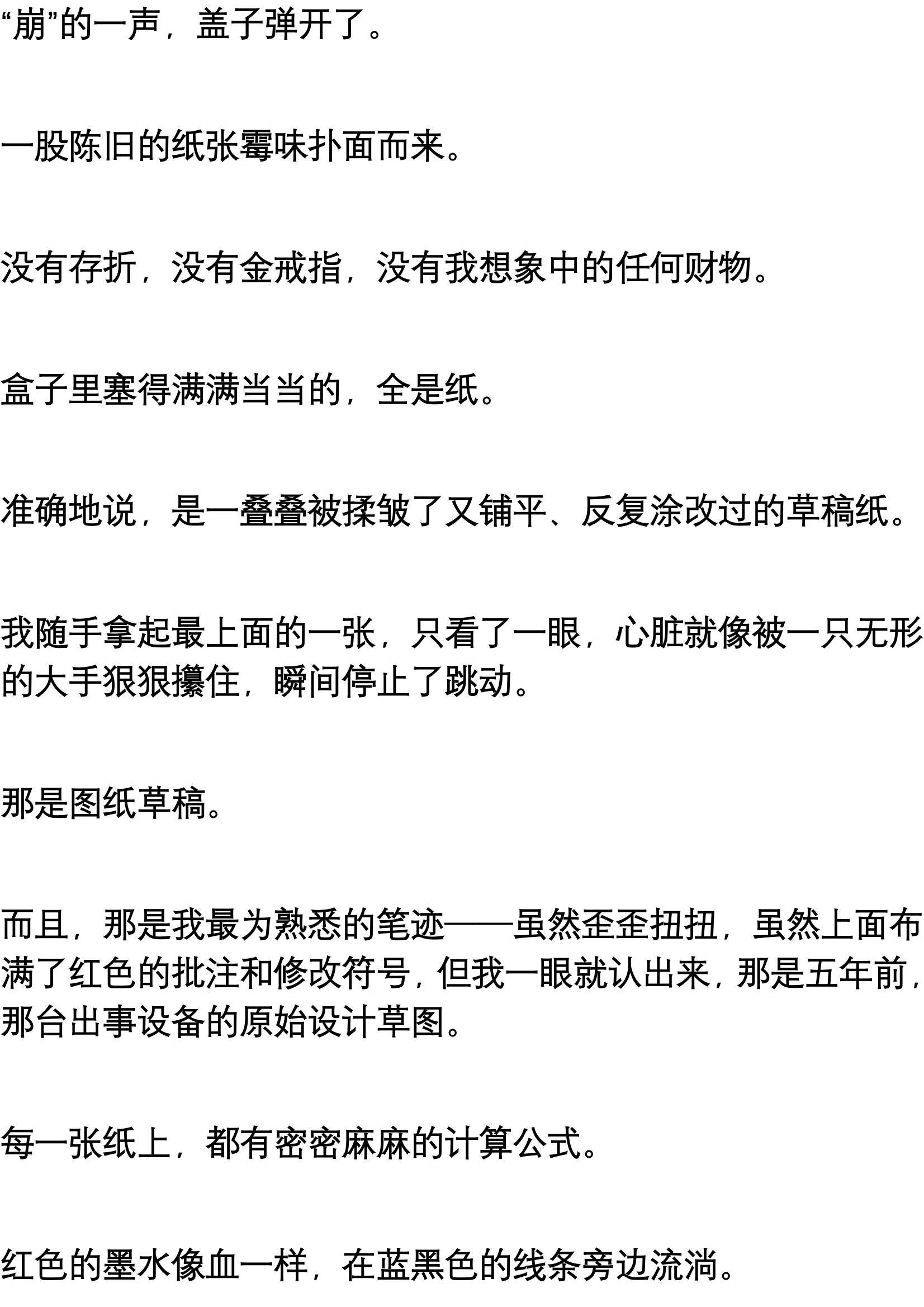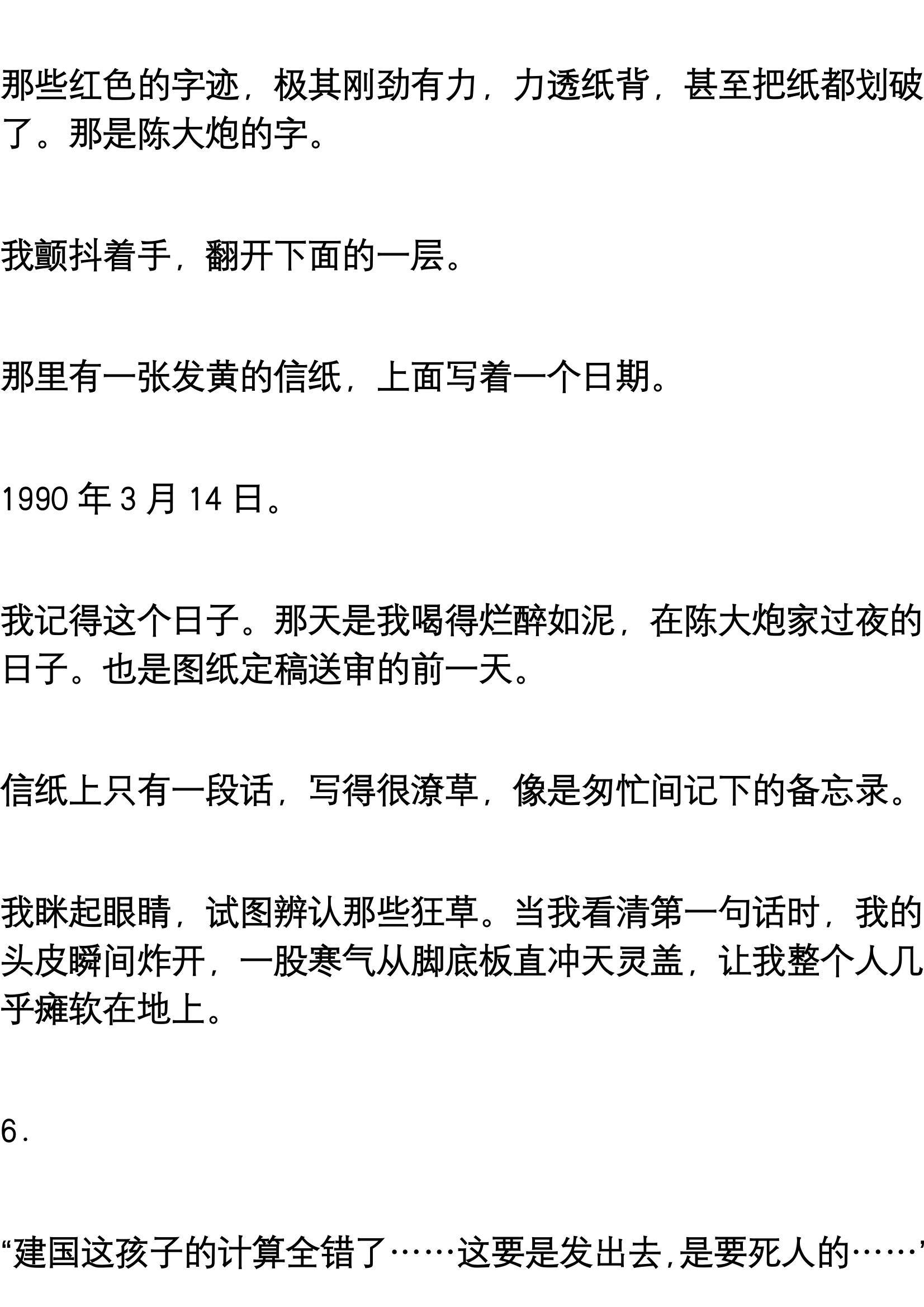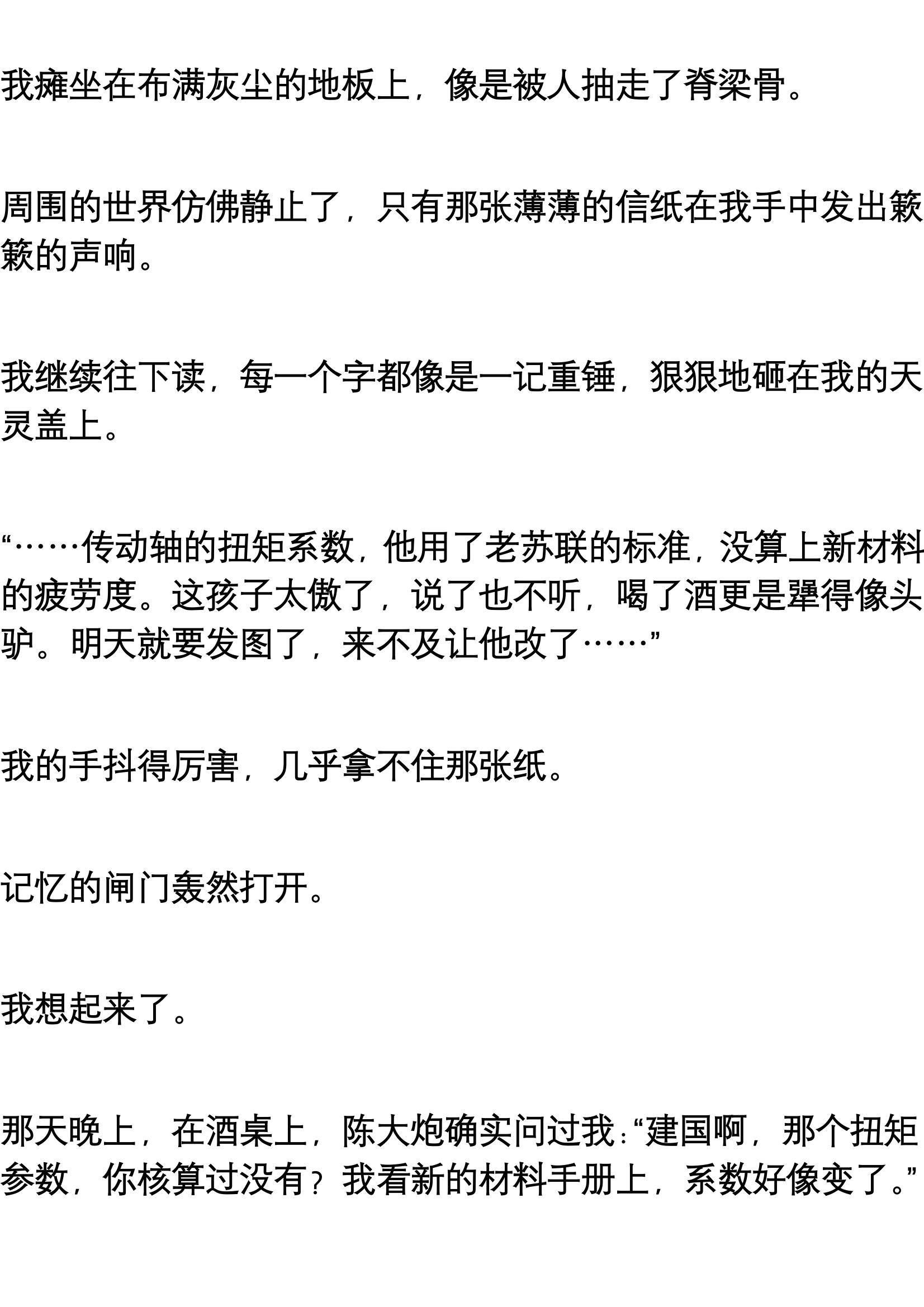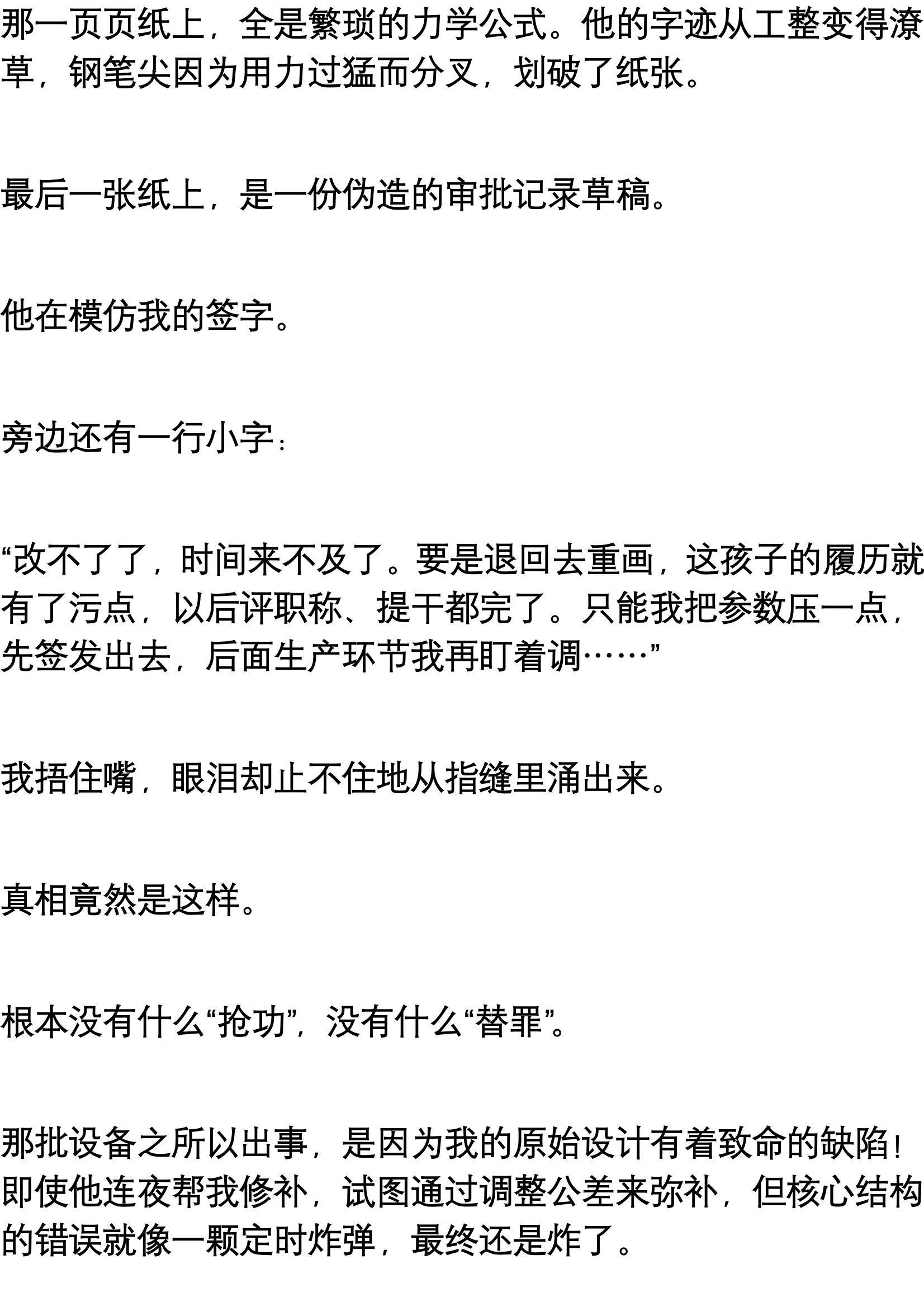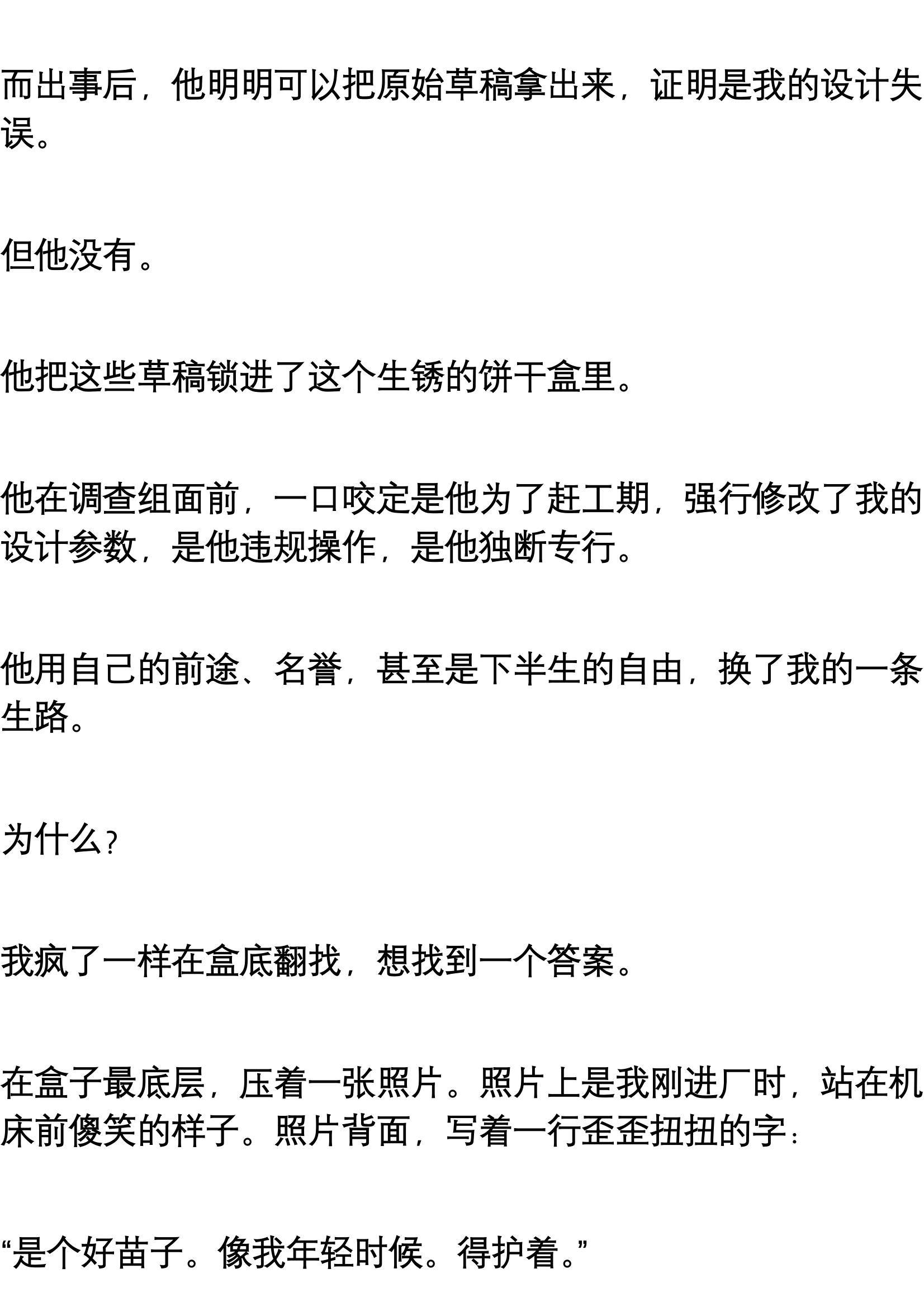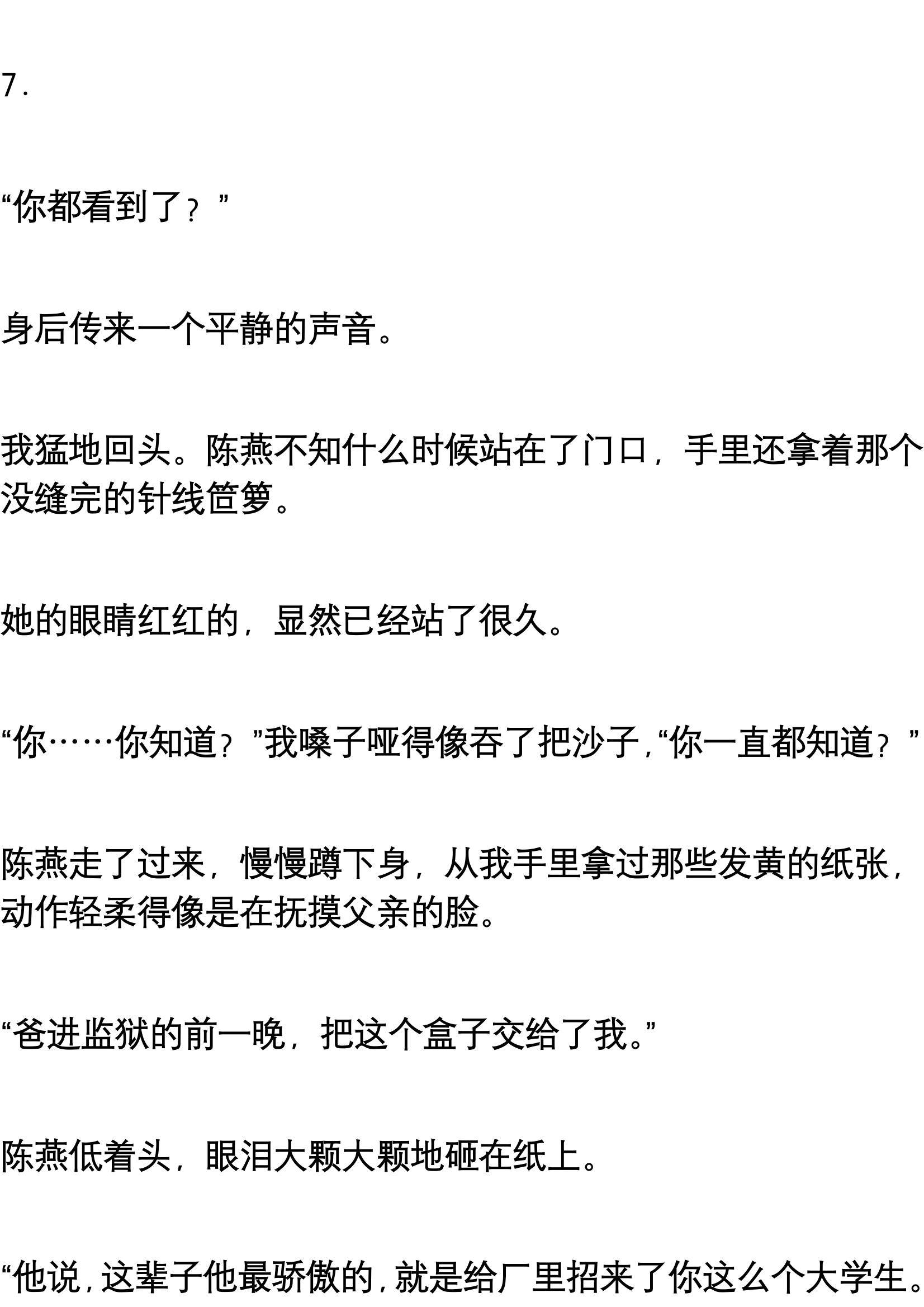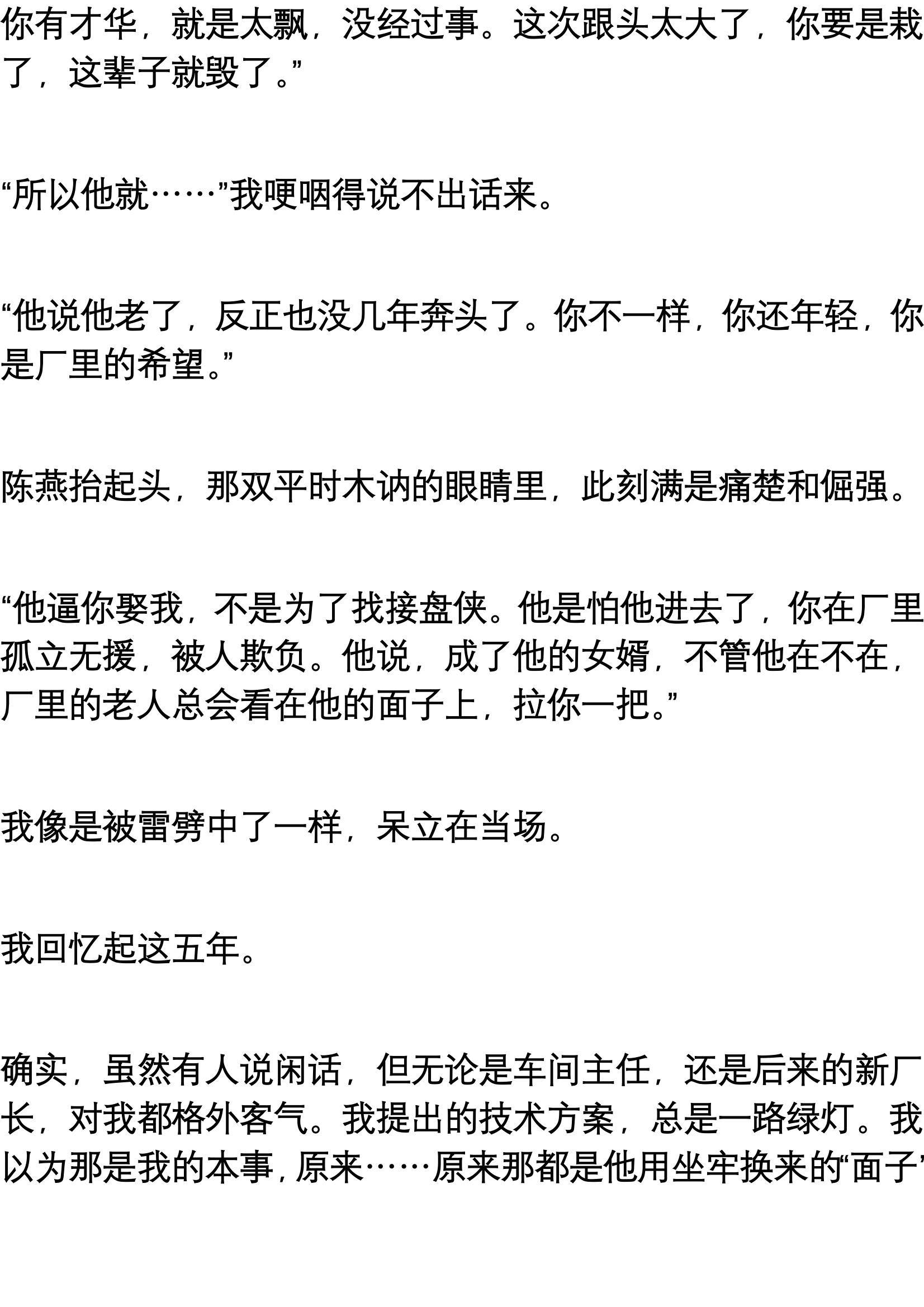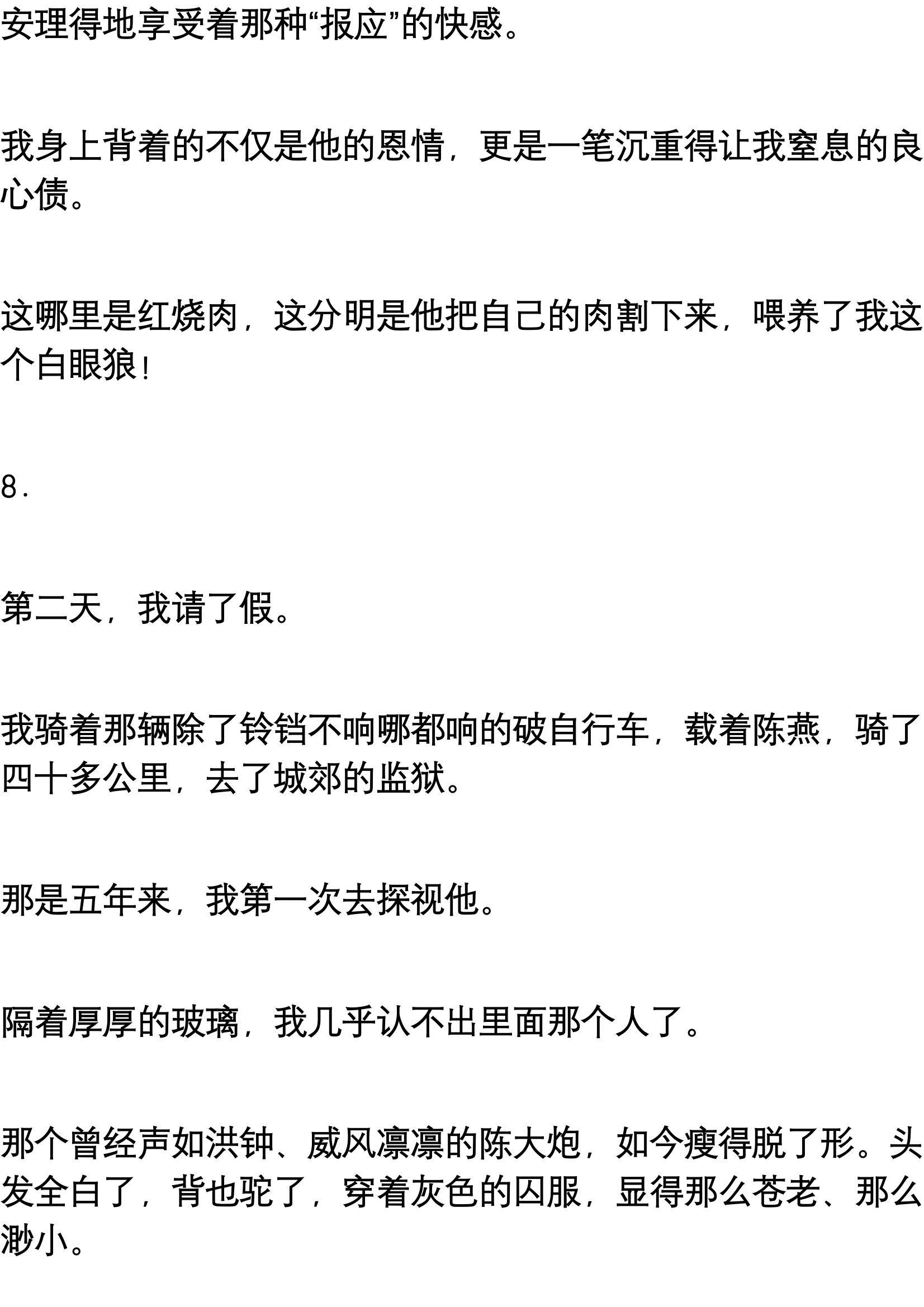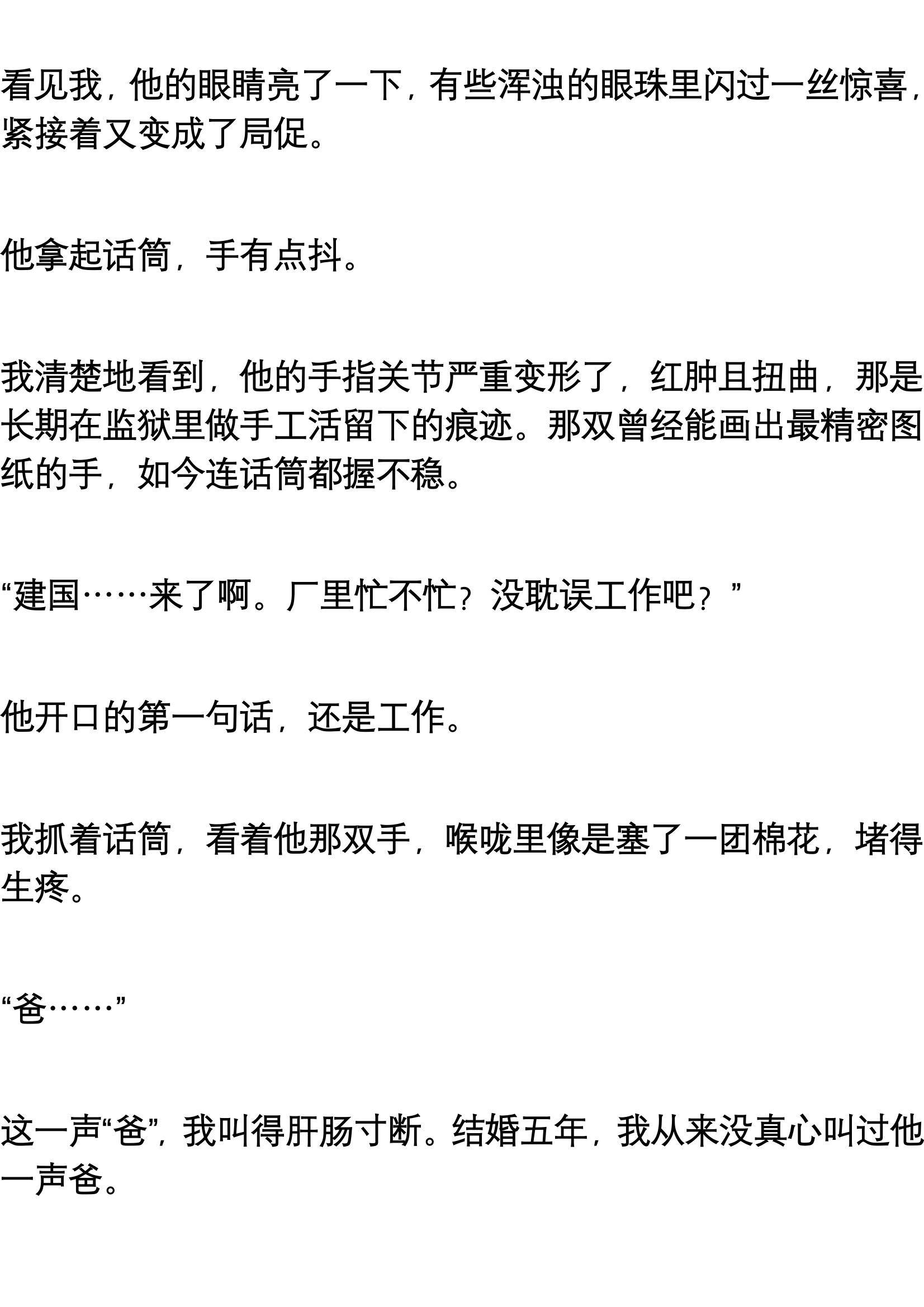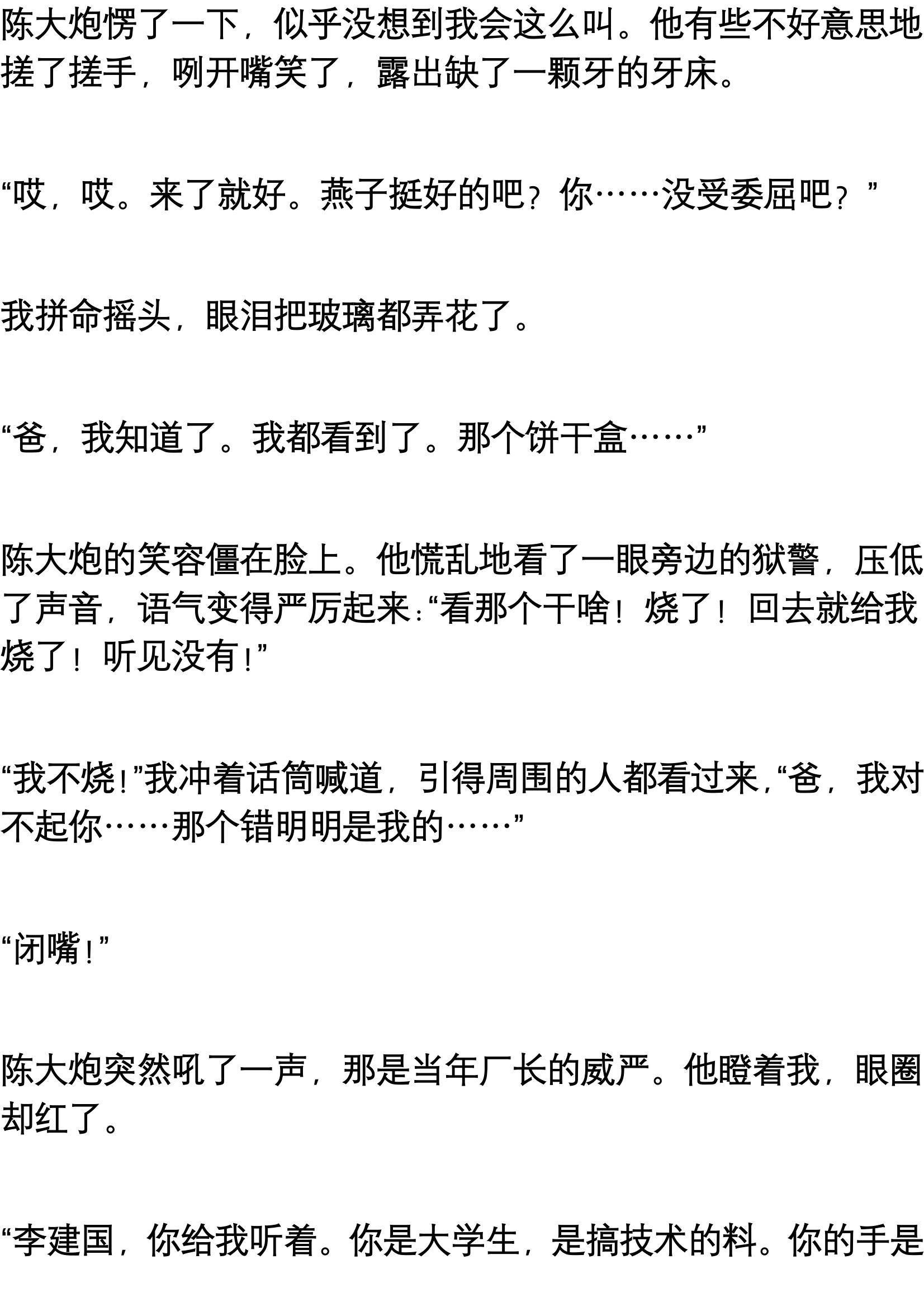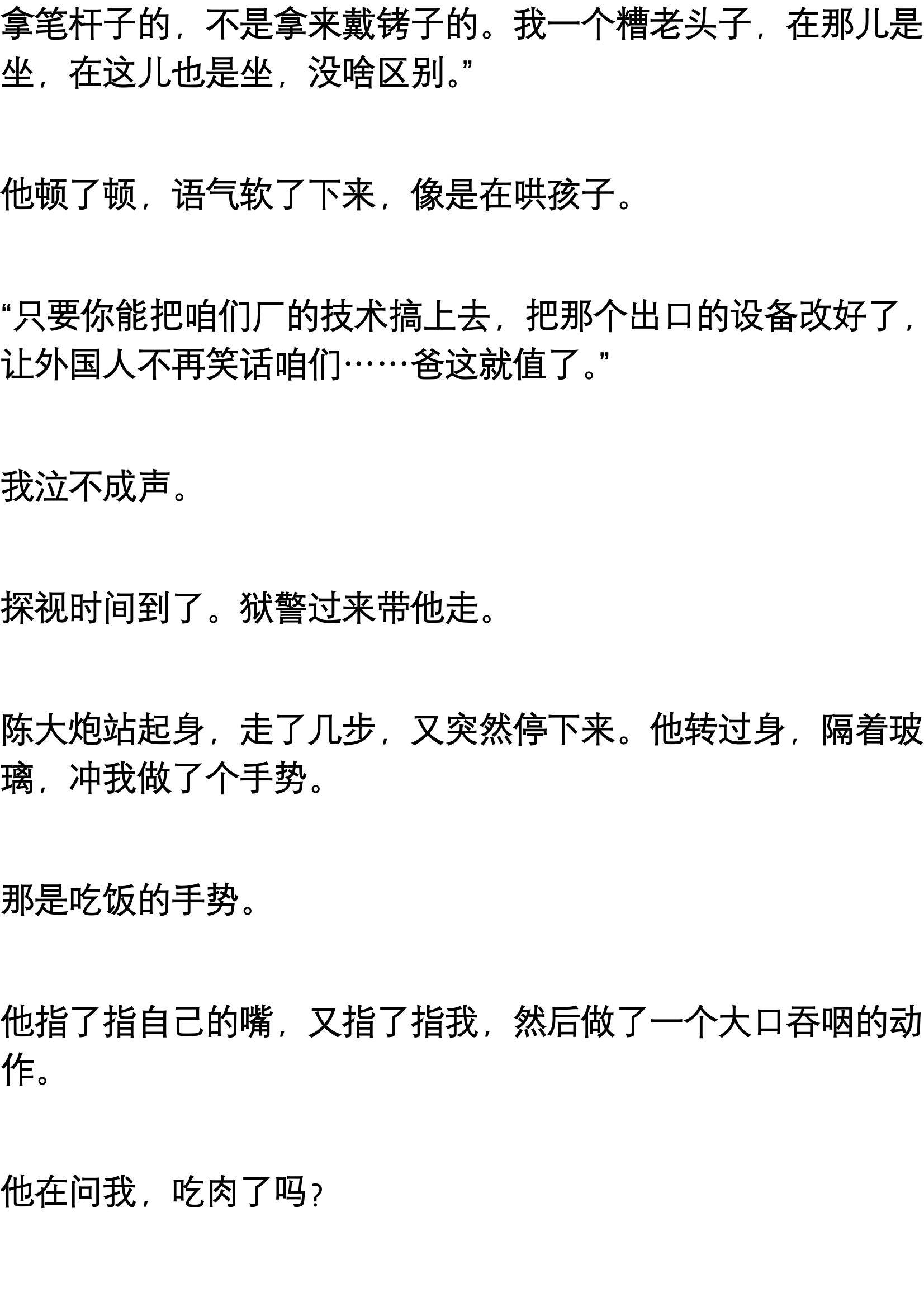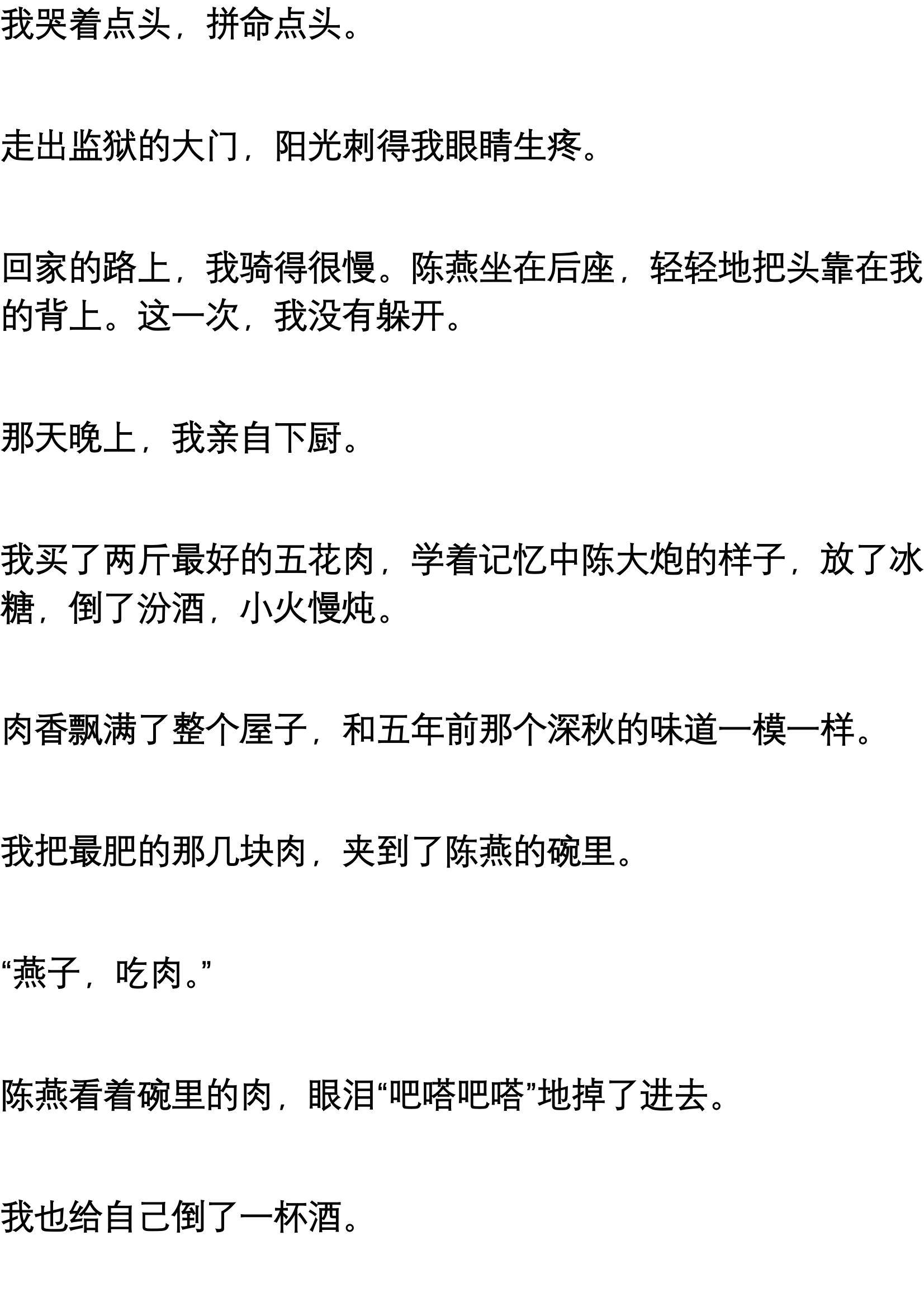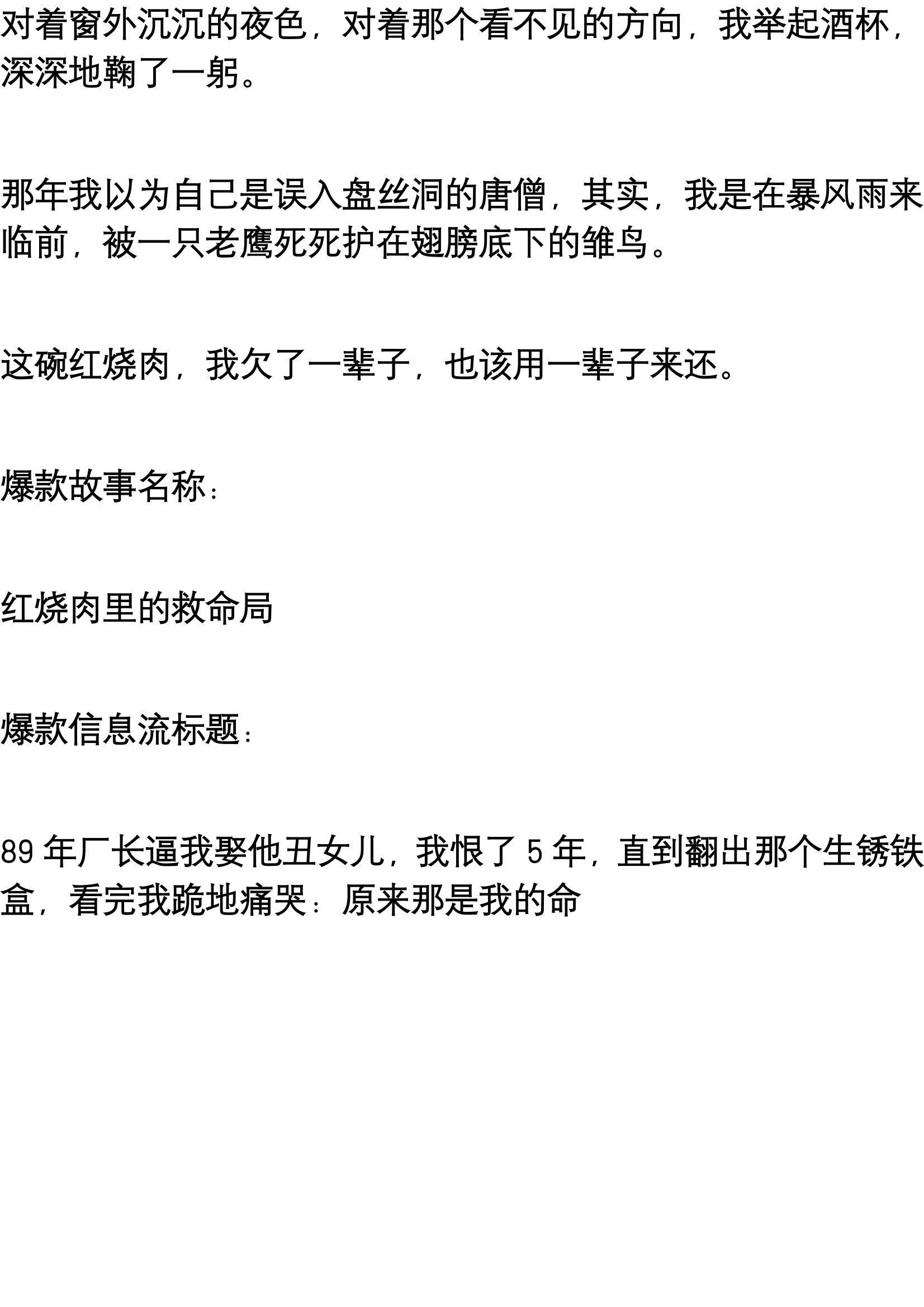1.
那是红烧肉的味道,混着汾酒的辛辣,像是那个贫瘠年代里最奢侈的诱惑。
我叫李建国,是厂里刚分来两年的大学生技术员。那时候我二十四岁,心气高,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,迟早要干一番大事业。可现实是,我每个月只有五十六块钱工资,住在四面透风的单身宿舍里,每晚听着隔壁车间的轰鸣声入睡。
改变我命运的,是厂长陈大炮。
陈大炮人如其名,嗓门大,脾气爆,在厂里说一不二。不知从哪天起,他开始频繁叫我去他家“改善伙食”。
“建国啊,读书人费脑子,得补补。”
陈大炮总是坐在那张掉漆的八仙桌前,手里捏着个酒盅,一边用筷子敲着碗边,一边哼着《沙家浜》。桌上那盆红烧肉炖得油光发亮,颤巍巍的。
我那时候年轻,馋啊。看着那肉,喉结就不自觉地滚动。
每次吃饭,陈大炮总是把最肥那几块夹到我碗里,自己只吃肉皮,或者用汤汁拌饭。他还总劝酒,那是高度的汾酒,几杯下肚,我就觉得自己是个英雄,把厂里的技术革新方案吹得天花乱坠。
陈大炮就眯着眼笑,也不反驳,只是不停地给我倒酒:“有志气,咱们厂的未来就靠你们这些大学生了。”
我就这么吃了大半年的红烧肉,喝了大半年的酒。
直到有一天,我在宿醉中醒来,发现自己躺在陈大炮家的客房里,而外面的流言已经传遍了全厂。
“听说了吗?李技术员昨晚在厂长家过夜了。”
“那是被看上了吧?厂长那个女儿,二十六了还嫁不出去,这是找接盘的呢。”
jrhz.info我当时脑子“嗡”的一下炸了。陈大炮的女儿陈燕,人老实,甚至可以说木讷,长相普通,在车间当统计员,平时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。
我去找陈大炮理论,觉得自己受了奇耻大辱。陈大炮却不像平时那么嘻嘻哈哈,他把酒盅往桌上一顿,那双总是眯着的眼睛突然睁大,透出一股狼一样的狠劲。
“建国,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你要是男人,就得负责。下个月初八,是个好日子。”
我看着他那张脸,突然觉得那大半年的红烧肉,每一块都是鱼钩上的饵。我被算计了。
我是个自尊心极强的知识分子,却因为几块肉,被这个大老粗绑架了下半生。
我娶了陈燕。带着满腔的屈辱和愤怒。
2.
婚结得很急,也很寒酸。
没有我想象中的盛大婚礼,甚至连几大件都没凑齐。陈大炮在这个厂里当了十年厂长,家里却并没有多少积蓄。
新婚之夜,我坐在床边,看着那个低头坐在红被面上的女人,心里只有厌恶。她就像个木偶,也不说话,只是手里紧紧攥着一块手帕。
门被推开了,陈大炮一身酒气地走了进来。
我以为他会给我一个红包🧧,或者许诺我个副科长的位置——毕竟我是为了他女儿才牺牲了我的前途。
但他没有。
他从怀里掏出一本红皮的小册子,那是厂里的《岗位安全操作规程》。册子已经被翻得卷了边,封面上沾着几处洗不掉的油渍。
“建国,”他把册子拍在我手里,力气大得让我手掌发麻,“别的我也给不起。这本子你拿着。以后干技术,记住四个字:胆大心细。”
我拿着那本破册子,差点气笑了。
这是什么意思?嘲讽我?嘲讽我这个大学生还需要看这种入门的东西?
“爸,我知道了。”我冷冷地应了一声,把册子随手扔在了床头柜上。
陈大炮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很复杂,我不懂。那时候我只觉得,那是胜利者的炫耀。
婚后的日子,正如我预料的那样,是一潭死水。
我在厂里拼命工作,想用技术实力证明我不是“吃软饭的”。我对陈燕很冷淡,经常在单位加班到深夜才回去。回到家,饭菜总是热在锅里,她已经睡了,或者假装睡了。
只有陈大炮,还是老样子。他在厂里依旧威风八面,但我开始有意避开他。每次在走廊遇到,我也只是公事公办地叫一声“陈厂长”。
我能感觉到背后那些指指点点的目光。
“看,那就是乘龙快婿。”
“切,还不是靠老丈人上位。”
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的脊梁骨上。我发誓,总有一天,我要摆脱这个“赘婿”的阴影,我要让所有人知道,我是靠本事吃饭的。
半年后,机会——或者说灾难,来了。
3.
那是一九九零年的春天。
厂里接了一个大单,是出口东南亚的一批精密纺织设备。这对我们这个老国营厂来说,是救命稻草,也是翻身的仗。
作为技术骨干,我主导了这批设备的核心传动结构设计。那段时间我没日没夜地泡在图纸堆里,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天才,居然能设计出这么精妙的结构,效率比老款提升了30%。
设备发货那天,全厂敲锣打鼓。陈大炮站在主席台上,红光满面,那是他当厂长以来最风光的一天。
然而,仅仅过了一个月,噩耗传来。
那批设备在客户工厂试运行时,发生了严重的断轴事故,导致两名工人受伤。客户方大怒,发函要求全额索赔,并追究法律责任。
消息传回厂里那天,天阴沉沉的,像要塌下来。
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断轴?那是我设计的传动结构啊!如果是因为设计缺陷,那我……我要坐牢的!
我疯了一样冲进资料室,手颤抖着调出了那批设备的终版图纸。
我记得很清楚,那个设计方案我是做过激进改动的。当时陈大炮还问过我稳不稳,我喝了点酒,拍着胸脯说绝对没问题。
我在图纸柜前翻找,冷汗把后背的衬衫都浸透了。
终于,我找到了那卷图纸。
我哆嗦着展开,目光死死地盯着右下角的签字栏。
设计:李建国。
审核:王工。
批准:……
那个“批准”栏里,赫然签着三个大字:陈大炮。
我愣住了。
按照流程,这种级别的图纸,必须要经过总工办审核,最后由厂长签字。但通常厂长只是走个过场。
我继续往下看,突然发现不对劲。
这张图纸上的数据……怎么和我记忆中的那个激进版本不太一样?有些关键的公差参数,似乎被微调过,变得更保守了,但依然保留了我的核心结构。
不管了,不管了。
我靠在冰冷的铁柜上,大口喘着气,一种劫后余生的虚脱感袭来。紧接着,是一股阴暗的、卑劣的庆幸。
签字的是他。最后拍板的是他。
他是厂长,他是法人代表。
出了这么大的事,总得有人扛雷。而那个人,白纸黑字写着,是陈大炮。
“老狐狸,你也有今天。”
我脑海里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。那一刻,我对他的怨恨,竟然奇异地转化为了一种报复的快感。
是你逼我结婚的,是你把我绑上战车的,现在车翻了,个高的顶着,天经地义。
4.
调查组进驻厂里的那天,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。
陈大炮被带走的时候,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慌乱。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
我就站在办公楼的台阶上,手里紧紧攥着那支钢笔,指节发白。
他在上吉普车前,停了一下,回头看了一眼。
人群熙熙攘攘,但我知道,他在看我。
那目光里没有怨恨,没有恐惧,甚至没有求助。只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沉重,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托付给我。
他嘴唇动了动,隔着十几米,我读懂了那个口型。
“照顾好燕子。好好搞技术。”
吉普车卷起一阵黄尘,开走了。
那一晚,家里静得可怕。
陈燕坐在沙发上,没有哭,只是在缝补一件我的工作服。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展露出明显的情绪波动——她的手一直在抖,针尖几次扎破了手指。
血珠冒出来,红得刺眼。
她也不擦,就把手指含在嘴里,吮吸一下,然后继续缝。
“你爸……可能是为了赶工期,疏忽了。”我干巴巴地解释了一句,试图掩盖自己内心的慌乱和愧疚。
陈燕停下手里的针线,抬头看了我一眼。
那眼神冷得像冰,又像是藏着一把火。
“李建国,你真的觉得,是他疏忽了吗?”
我心里一跳,强撑着说:“图纸上签的是他的字,白纸黑字……”
“睡吧。”她打断了我,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死寂,“明天还要上班。”
陈大炮因为玩忽职守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,被判了七年。
他进去后,厂里进行了大清洗。但奇怪的是,我这个“主要设计者”却奇迹般地保住了位置,甚至因为在那次事故后的整改中表现突出,被提拔为了技术科副科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