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了十年小学,突然要我去教高中?王涵梓的焦虑藏在电话里。8月10日,山东临沂某小学英语教师王涵梓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通知,手指微微发抖。这条要求“有高中教资教师明日参会”的短信,像一块石头压得她喘不过气。散会后领导单独留下她:“这是锻炼机会。”可她心里清楚,从教小学到高中,哪是简单的“锻炼”?

转岗暗流在临沂并不少见。陈栋梁所在的九年一贯制学校直接摊牌:2032年前,所有有高中教资的老师必须去高中任教。这个时间节点背后,是2016年二孩政策带来的入学高峰——2032年,这批孩子将涌入高中。

学龄人口减少就像涨大水,小学在一楼,初中在二楼,高中在三楼。陈栋梁打了个形象的比喻。他自愿报名转岗,因为“去三楼更安全”。但并非所有老师都愿意当“逃生者”,音体美老师踊跃报名,主科老师却望而却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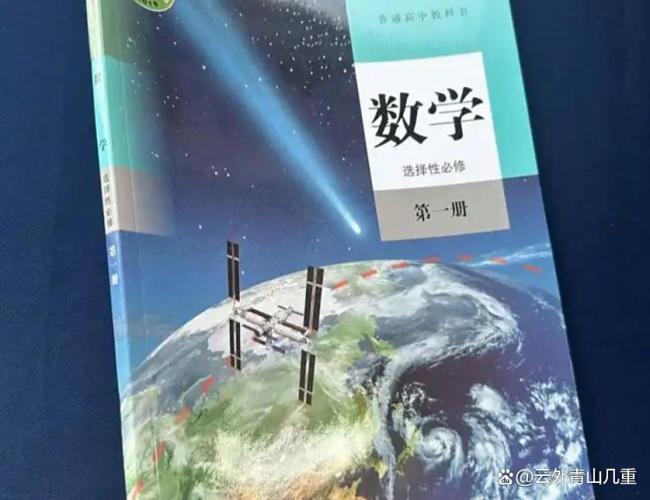
刘敏翻开高中数学教材,函数单调性的推导让她直冒冷汗。“初中教的是零花钱买苹果的例子,高中要严谨的数学证明。”这位乡镇初中数学老师发现,自己连课后服务费带补贴每月能拿近2000元,转岗后反而要少近2000块。

家长质疑更让刘敏心寒。当听说新调来的老师多来自小学初中,有家长直接要给孩子转学。“我们不是不努力,是真的怕耽误孩子。”她在电话里说。

临沂的困境早有预兆。2022年山东机构编制网就预警:入学高峰过后教师需求将骤减。当地采用“潮汐式”调配:小学高峰多招,初中高峰选调,高中高峰调剂。2023年《大众日报》披露的数据显示,临沂已通过这种模式调配教师数千人。
这种“潮汐式”调配正在全国蔓延。江苏近3年调整1600名教师,福建永安组织转岗培训,宁夏、江西等地发布转岗公告。中央编办更在2022年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支持跨学段任教。
湖州师范学院调研发现,74位跨学段教师中,无人适应新岗位。有初中数学老师坦言:“高中函数教学需要严谨推导,这和初中兴趣培养完全不同。”
华南师范大学刘善槐教授指出:“教师不是砖头,不能随便搬。”他建议建立动态工资制度,体现不同学段的工作强度差异。但现实是,多数地方仍采用“一刀切”调配。
杭州富阳区的探索值得借鉴。他们开办跨学段师资培训班,将50名小学老师培养成“能上能下”的复合型教师。这种“前3年教小学,后回初中”的模式,既缓解了学段压力,又保留了教师适应性。
刘善槐提出更根本的解决方案:将班额从45人缩至25人以下。但这个建议遭遇现实瓶颈——“县里财政能否支持新建教室?”成为横在改革前的现实问题。
福建某县小学老师张丽,整个暑假都在复习高中教资考试。“县教育局鼓励考更高资格证,这是我们最后的筹码。”她翻开堆满书桌的复习资料,眼神坚定。
王涵梓最终接受了转岗安排,但每晚都在看高中英语网课。“我不能让学生觉得,我们这些老师是来‘混日子’的。”她打开教材,对着“从句结构”章节标记重点。
当学龄人口排浪式退去,留下的不仅是空荡荡的教室,更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阵痛。这些被迫转岗的老师,他们的迷茫与挣扎,或许正是中国基础教育转型必须面对的考题。





